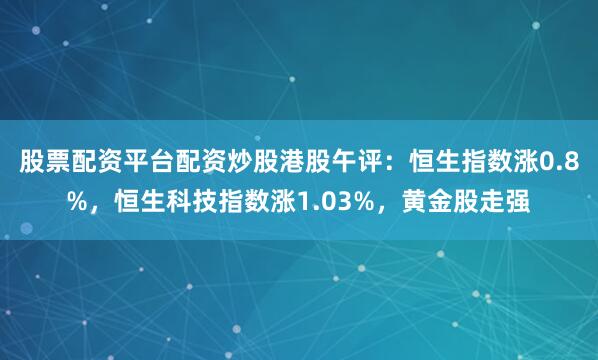三轮车上的泪痕
北京的冬日向来凛冽,寒风如刀,刮得人脸生疼。一九五四年的这个下午,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吱呀作响地碾过积雪未消的胡同,车上坐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,正是年届九旬的齐白石。老人裹着厚重的棉袍,双手紧握着一卷画轴,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
车夫在一条熟悉的胡同口停下,齐白石颤巍巍地下了车。他抬头望向那座曾经熟悉的院落,却见门楣上赫然挂着\"悲鸿故居\"四个大字。老人浑浊的双眼突然瞪大,枯瘦的身躯如遭雷击般剧烈颤抖起来。他踉跄着向前几步,干枯的手指抚过那冰冷的匾额,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。
\"这...这是何时的事?老人喃喃自语,声音嘶哑得不成调子。
展开剩余69%院门虚掩着,齐白石推门而入。庭院里的老梅依旧,只是少了那个常在树下作画的身影。他缓步走过每一间屋子,指尖抚过案几上的笔墨纸砚,每一件器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离去。画室里,一幅未完成的奔马图静静地躺在案上,墨迹早已干涸。
老人颓然跌坐在太师椅上,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他想起四十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冬日,时任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踏着大雪来到他破旧的画室。那时的齐白石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画匠,靠着卖些鱼虾小品勉强度日。
\"白石先生,请务必出任我校教授。\"徐悲鸿执着地三顾茅庐,雪花在他肩头积了厚厚一层。
艺专的教员们对此嗤之以鼻。\"一个乡下木匠也配教我们画画?\"流言如毒蛇般在校园里游走。有人故意在他的画作上泼墨,有人在他讲课时高声谈笑。三个月后,齐白石黯然辞职。令他没想到的是,徐悲鸿竟也随即挂冠而去。
\"他们不懂先生的笔墨。\"徐悲鸿将一册新印的画集递到齐白石手中,\"但世人终会明白。\"
此后岁月里,徐悲鸿每月都会亲自送来润笔费。夏日备风扇,冬日置火炉,连画纸都要亲自挑选。最让齐白石难忘的是那个元宵夜,徐悲鸿携酒来访,二人对酌至天明。微醺之际,徐悲鸿忽然叹道:\"白石兄笔下鱼虾,看似简单,实则每一笔都暗合天地至理。那些俗人,如何能懂?\"
老人颤抖着手从回忆中抽身,环顾这间空荡荡的画室。案头日历停留在1953年,上面用红笔圈出的日期正是徐悲鸿最后一次来访的日子。直到此刻,齐白石才恍然大悟——这一年多来,每月按时送来的钱款,原是徐君临终前的安排。
夕阳西沉,将老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他缓缓展开带来的画轴,那是一幅新作的《虾戏图》,墨色淋漓,虾须纤毫毕现。老人将画挂在空荡荡的墙上,对着虚空轻声道:\"徐君,最后一幅,给你看看。\"
走出院门时,风雪又起。齐白石站在三轮车旁,最后回望了一眼那座寂静的院落。\"生我者父母...\"老人声音哽咽,\"知我者...徐君也。\"雪花落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,与泪水混在一处,分不清彼此。
三轮车渐行渐远,消失在胡同尽头。两位大师的友谊,如同这冬日里最后一片雪花,纯净无暇,终将化作春水,滋润后世艺坛。今人观其画作,仍能感受到那份超越时空的相知相惜——艺术之真谛,不正在于此么?愿天下知音,皆能如徐齐二人,以诚相待,以艺传情。
发布于:山西省淘配网-低息配资官网-股票配资平台-合规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